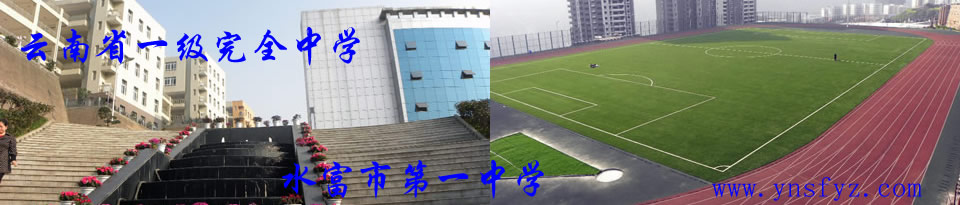今天是:
没有任何调查
老家啊老家
老家的距离要有多远,才足以构成思念?
常常设想:若没有二十年前的那次背离,老家的种种会时时萦绕梦境么?
那么思念和距离注定是分不开的了。
二十年前,我生活在老家??贵州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县城的历史还算有些旧,四个古城门便是明证:城门上的藤蔓垂吊,蒙受厚厚的尘埃,略显沉重的摇晃中满是岁月的叹息。还记得小时候出入最多的是西城门,因为一出西城门就是一条河,那里是童年夏季的乐园:河水清澈逶迤,小鱼细虾清晰可见,还有一种像极蜻蜓却比蜻蜓体型瘦小许多的被我们称为“阳剪刀”的昆虫,薄纱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蓝紫的光芒??那是能让我惊呆很久的一种色彩。好几次想捉住一只仔细看个究竟,但是记忆里却从来没有成功的记录,大概如此美丽的精灵是有天佑的,容不得俗手玷污。很多年后,徘徊于这条河的堤岸,同样地季节,却再也看不见它了。问河边居住的人,摇摇头,不耐烦地进屋去了。那时,夕阳的余辉铺洒在柔软的河面上,倒映着沧桑坚硬的古城垣,我的心啊,被一种叫做“阳剪刀”的昆虫搅动得凄凉不已。
后来,很少出城门了,读书忙了,人也长大了,不会因为炎热就肆无忌惮地穿着小褂子花短裤跳进河里贪凉。其实,县城不大,南门和北门之间就一公里多的路程,两者连接的是主街;西门和东门的宽度距离就更短了。但是那个时候人心谨小,出了城门就叫“出城”,总会在心里生出几分不安,出了城的人一到天擦黑就忙不迭地往家赶,城外如同荒郊野岭让人凄惶逃离。记忆中有几次出南门,是有一远房亲戚住在南门城外,每次见着那个和善的中年妇女,母亲就让我叫她“姑妈”,她并不是我父亲的姐妹,这不要紧,关键是她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四次喜宴,我一次都没有落下。那年月,有酒席我是相当愿意和母亲同往的,即便是上了高中,个子都超过母亲了,依然挽着母亲的手,一番客套寒暄后,真正让我神往的是那一桌子菜,每次我都吃得很上心也很小心,怕爱面子的母亲难堪便要小心;面对难得的荤菜又不能亏待了肚子,就得上心。每次散席,回家的路上,母亲总要淡淡地问有没有哪个菜没有吃到,我的回答从来都是“都吃到了”,母亲便露出淡淡的笑。她希望孩子吃得好,但又不能太露饿相丢人。我似乎第一次吃酒席就知道了母亲的这种心理,所以尽量符合她的要求,这也是母亲每有酒席总喜欢带上我的原因吧。我听到母亲在家骂过父亲,就为父亲在酒席上吃出“喉耳包”(脸颊因嘴里食物太多而鼓起),说父亲连个娃娃都不如。那个娃娃就是我,那时的我对父亲满是愧疚,觉得是自己害父亲被骂。父亲后来不太愿意吃酒席,说吃也吃不清净,拈一夹菜就会被母亲在桌底踢一脚,不如不吃的好。后来即便去了,父亲也不愿意和母亲同坐一桌,我特别理解父亲。
离开老家后,我也遭遇过很多酒席,都是朋友同事的,可以随心所欲了,却怎么也没了胃口。
初中时,搬过一次家,搬到父亲单位的房子。父亲那时在水电局工作,住在那里水电相当便宜,象征性地交点钱,几乎是白用,这很契合一向节俭的母亲的意。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房子楼层都不高,
有三层高的不多,我的新家就在顶楼??三楼,后阳台和北城门隔一条小路的距离,每天走向阳台,就能看到城门顶部仿佛长了几个世纪的植物??这些植物没有季节特征,永远灰蒙苍老,即便是随意垂吊下来的藤蔓,枝叶似乎永远来自暮秋。我曾经怀疑它们是否活着,但仔细打量,总有几点若有似无的绿顽强地证明着生命的迹象。北城门曾经是和我距离最近的城门,但是北城门却也是我最陌生的城门,因为我几乎没有走出过北城门外的地方。夏天很热的时候,我爱看那些云朵,看它们是不是往北城门更远的方向飘。父亲说云往北面走,就是?破瓦房。我就希望那些晃晃悠悠的云别朝那方走。那些日子,看云的眼都酸涩了,北城门远方的天空也被我读得烂熟于心,夏天总是晴天多,云走的方向也执着。
很多年后,当我的爱情从云朵深处的那个方向款款而来时,我似乎才明白了一些远和近的玄妙,明白了那些云朵的执着。
离开老家的那年,我24岁,怀揣一份调令,准备到一个陌生的小城,为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客车驶出东城门??最热闹的城门,这里连接着外面的许多城镇,连接着一颗颗不安分的心。它见证了太多出出进进的悲喜,拱形的门洞在夜晚黑成一个慵懒的呵欠,流露出对凡世的不屑和嘲弄。我就从这个呵欠中走出,神色庄严中藏有一丝难以遏止的对未来的憧憬。一走就难再回头,一走就是无尽的岁月,一走就被东城门延伸出的手送出游子模样……
时空把老家间隔得烟笼雾罩,我不知道二十多年的生活记忆如此顽强勃发,它就像一个成心捣蛋的孩子,在你生活的某个空隙里扔一颗石子,让人陡然一惊。我可以不相信一切,但我知道那些梦境的诚实。在那些梦境里,我永远走在上学的路上,永远是父母年轻疲倦的面容,永远停留在“阳剪刀”翩飞的夏季……我惊异地发现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的一个比较:前二十年很长很长,后二十年很短很短。长倒不是难捱的漫长,短也不是快乐的缩短。现在啊,带一届学生毕业就是三年,计算的单位大了。试想,再年轻的日子,禁得起多少个三年的叠加?在老家的那些日子,是不用计算的,该来的来该去的去,日子流走的声音温婉可人,日子流走的背影绰约袅娜……比不得现在,时间的滴答声锯齿般尖利,催促镜中的容颜莲花般开落。
一年中,总会抽点时间回老家呆上几天。闲来走走逛逛,感觉是越来越陌生了??那些熟悉的老房子早被新楼替代,街上的人比过去多得多,而且基本上不认识。不像过去,走在大街上的人基本上都认得,即便叫不出名字也知道他(她)要么是卖糍粑的,要么是杀猪的,就连街上的几个叫花子也知道他们姓甚名啥。所以我常常会在老家的大街上迷失几秒钟,失落是难免的,可是面对日益强大的城市巨变,这点失落实在渺小,渺小到不好意思说出来。
一个夏天的黄昏,我走上老家的东门大坡(贵州山多,多到“山”被称作“坡”)在那里可以俯瞰全城。我努力找寻记忆中老家的印记,那个被四座城门围起来的形状是我熟悉的,就像一个旧碗盛装着不熟悉的菜肴;再就是视野所及的东城门了,白天里,它的门洞灰灰的,灰成一个被打断的呵欠,被吞吐的车辆和行人。我似乎理解了它的疲惫:它作为古迹被保存下来,却没有翠树青石环绕,没有禽鸟啁啾和鸣,仅有厚厚的尘土和一块提示古迹的石碑以及没完没了永无止境的喧嚣。看老家的心绪总是怅然的,仿佛在骨肉中慢慢剥离一层东西。山上南风温柔,却将我轻易吹倒!
总是要走的,父母的身影在车窗里越来越瘦小,挥动的手也变得犹犹豫豫,泪水总在转过身子的刹那决堤。当车窗外面全是山岗田野,心才能慢慢沉静。我不知道老家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是只要有那四座城门的圈佑,有我年老父母的气息,有二十多年的成长记忆……老家就是我永远的牵挂永远的痛。
车厢里,郑智化苍凉沙哑的歌声痛彻心扉:我用一转身离开的你,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老家啊老家!
注:该文获2011年云南省中小学师生文学作品大赛优秀作品奖,并获得全国第十届“中华情”散文类作品一等奖,发表在2011第四期《金沙江文学》上。